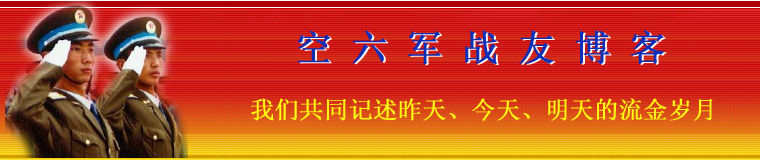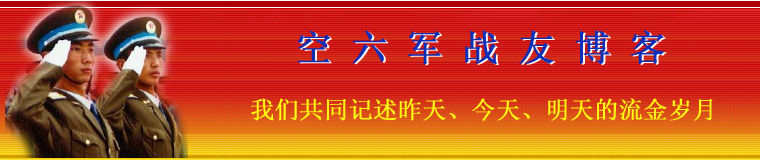|
前面的话:雷达33团战友回忆录《北国春秋》的发布会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召开了,这对曾经33团的官兵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和值得纪念的事,也是全体空6军战友们当贺的一件喜事。值此,将曾贴出、又被“黑过”、现在仅剩六分之一帖文却还在网上挂着的《 北京向北的那些事儿 (一)--(六)》再次贴出,算是本人对雷达33团的一份贺礼吧。同时,也希望这些字别再一次被“黑”。谨此,向当年大草原上的雪达兵战友们致敬! 眼下还没机会读到33团此经年大作,但想其中定是记述了苍莽草原之上士兵们那一段段如歌火热的军旅岁月和大漠深处一批批边防雷达人不凡的身影和闪光的脚下之路。
重拾记忆中的碎片,却唤起了虽曾久远、早己镶刻于心的“ 北京向北的那些事儿---- ”
一、北京向北
北京向北,欲进入草原,必经过那座因“大境门”而闻名的城市张家口,张家口再向北就是当地老乡们地理概念中的“坝口”了。所谓“坝口”,其实是个相对模糊的方位概念。“坝口”的确存在,但要准确定位却很难。就像你站在自家门里说这是家门口,可以。站在门口外说这是家门口,也行。里外都是视当时表述者所站的位置而定。“坝口”在地理上没有严格的定义,但何为坝上,何为坝下,只要你往这儿一站就显而易见,不言自明。在这个北京向北,大概北纬41-42°的地方,自西向东横亘着平均海拔1500-2500米高度的一道状如台阶、徒然升高的“坎”,坎的北向叫“坝上”,坎的南面就是“坝下”了。这里是华北平原与内蒙高原的交汇之处,是农耕文化和畜牧文化的融汇之地,当然更是千百年来兵家必争的古战场和见证生死博杀的要冲之地。
至坝口,便见断崖如韧,沟壑似壁。大展开面空间的二级台阶之上,行行列列布满了金字塔样白色的防坦克水泥三角形巨桩,视野内望去,无始无终。如韧的断崖是人工爆破所为,TNT己将昔日那连绵的南向山坡炸成了一个个巨大无比的超级天然跳台,被火药撕裂开的壁面显得狰狞恐怖,断崖齐刷刷的挤在一起如“金刚”般呲着的利齿,个个都泛着黄涩的幽光。细如腰带的一条公路由南向北如蚯蚓般爬行其中、徐徐向上漫延着,这是连接坝上与坝下、草原和内地惟一的一条公路通道,就这,一旦大战在即也是要首先被炸断炸掉的。
为了防止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坦克摩化部队经外蒙南下大举进犯并直抵我京都门户,共和国疮伤巨痛中的统帅们,创造性地沿袭了始皇帝的长城御敌之术,在这方圆不及百里的地域之内为既将可能来犯之敌预设下了这个巨大的门坎和陷阱,并于此屯兵无数,其中不乏为共和国打下江山的精锐之旅。
张北的这道“坎”是北京城最北边最大的一道天然“大门坎”,相对首都而言,这是我北方御敌的最后一个天然屏障。那如长城列阵般、里三层外三层摆放着的水泥三角形防坦克桩,也都是为老毛子们的坦克备下的,就单等着那些庞然大物们自己个儿撅着腚爬上去后,再自己将自己顶起来,落个高低不就架弄着自残于此。然后,这坝上坝下的军民们就可用孙玉国们在珍宝岛上使过的招儿,用爆破桶和肩扛式火箭弹,再用董存瑞们用过的炸药包,再用大口径的山炮对着老毛子这些只能撅着腚在原地打转儿的乌龟壳们一顿滥炸,将毛子们的铁骑迟滞并消灭于此。否则,那毛子们的机械化部队将顺山就势由北向南无碍推进,不消一天功夫就可达至宣化、下花园一带。那样首都将无险可守,北京会危在旦夕。
中苏交恶于六十年代之初,交火于乌苏里江的珍宝岛。按统领们的推断,第三次世界大战也必将始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亡我之心不死”。大战既开,进攻定是由老毛子的坦克摩化部队和重型轰炸机群平行立体推进,定是由北向南一路炸向北京、一路碾向北京,定是以抢战我首都为战争的首要核心,新的世界大战战争的口子也必将由此处撕扯而开。
做为战场预设,北京向北,对世界革命红色的心脏而言其实并无战略纵深可谈,战争的火药桶一经点燃,伟大领袖毛老人家的七亿人民七亿兵,同来自西伯利亚的毛子兵们只能于此博死一战,绝无二选。
二、无从确认过的推断
军人本为战争而生。战争一旦打响,对草原上那些身处边防一线位置的雷达连和边防连队中的一个单兵而言,他们的战场位置、战争价值在哪?他的战场角色又是什么?他们的战场能动性该如何体现出来?当年,曾就此话题向不少雷达部队的干部和可爱的小兵们询问过,结论既是没有结论。那个年代中,被“伟大精神原子弹”武装起来人、包括我们的一些干部和战士,要么照实回答“没想过”,要么就是给你天上地下的一通儿不着调的“胡抡”。更为经典的是,曾和一位我很敬重的首长谈及此话题,首长不假思索、且自信满满地告诉我:“党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真理。绝对的真理!但却让我无语。
雷达荧光屏上的显示清晰可见,仅敌“乔巴山”一个机场每天呼呼啦啦起降的战术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就己对我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乔巴山”,老毛子空军重要的战争机器储备基地,其南北相向于北京而言基本处在同一个垂直的刻度上,直线距离仅与长春至北京相等,从“乔巴山”至北京,锡林浩特恰在其延长线的二分之一点位上。
老毛子们的飞行技术确实了得,“压线飞行”在标图板上记录的航线轨迹就如同在国境线上不断重复着、准确地一次次的描边飞行。那个时候的战争理论构成和战争形态分析虽然还没进化到现在的什么“信息战”、“超限战”、“外科手术式精确打击”阶段,但仗一旦开打,转瞬间这一线二线的雷达阵地你就得经受老毛子导弹第一波攻击却是不争的事实。待战术轰炸机再飞至头顶往下甩炸弹时,这时的阵地上早己是狼烟四起,火海一片,这次一波的攻击无非是老毛子们为地面的长驱直入扫清障碍而巳。
那战争爆发最初始阶段的雷达连又能干些什么呢?他的战争价值又是如何的体现呢?不用想的那么高远,结论其实非常简单。如果在战争的引信处于即将点火之时,在敌强磁和强电子的干扰之下,你能将有效空情快速上报、能将第一批次敌情准确给发出去就已是万幸,至此,做为一线的边防雷达站,你的战争使命在这时其实就己经完结了。如果还能乘着老毛子们的导弹在天上往这飞着、没掉下来的那几分钟的宝贵功夫,自己个主动甩两手榴弹把雷达车、发电机、天线和储油罐先给炸了,好歹也算是可以保留点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和减少日后自己心里的那份憋屈。剩下的事儿就是抄起“五四式”和“五九式”化军为民,化整为零,混迹于牧民,“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敌后打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了。
结论有些过于残酷,但却无可辩驳,也无需再做“推断”和“确认”。不开第一枪的自律准则和在装备科技上处于劣势守势的军队,在战争之初你只有挨打和招架的份儿。“精神原子弹”在战场和物理意义上、在和铁与火的碰撞中是无法同高科技和核裂变相题并论的。
转瞬之间原有的战场形态发生了根本变化,原来的一线二线变成了三线四线甚至无线可言,旧有的前方变成了敌后,成建制的军人变成了“散兵游勇”,技术的兵种被突如其来的战争强加变成了骑马挎枪走天下的游击战士。边防一线雷达兵们真正的、更加残酷的单兵反击作战和敌后战场生存才刚刚开始-----
以上,所幸没有被历史真的确认过。祝福我们边防一线二线的雷达兵!祝福和平!
三、再向北
再向北--- 待置身镶有国徽的界碑处转回身来再看,己是面向伟大祖国,腚朝外蒙和苏修了。
陪同而来的几位陆军兄弟此时颇是有些紧张,尤那位长相极富喜剧感的广东籍老哥为甚,操着“叽、叽、叽”我听不大懂的鸟语大概是说“多一步都不能再往前走了!否则....”。我想,当时这几位仁兄肯定是后悔酒桌之上口出狂言,答应将这位穿蓝军裤的带到了这个永远充满是非且变数无常之地。
掏出上海产“牡丹”,每人递上一颗,说:放心吧兄弟们!别说对面荒无人烟,往好了说也就是个“乌云其布格”。你就是现在在“线儿”的对面摆上一个如花似玉金发碧眼的“娜达莎”咱也不会越雷池一步的,除非是伟大领袖发号召将当年划拔过去外蒙失地收复回来。
大草甸子上界碑的那边,黄草齐腰,苍苍莽莽,天高地阔,廓寂无声。
草棵中,主人模样儿的短尾地鼠用贼一般的小眼晴朝这边鼠眉地看过来。
靠!看什么?面前这片无垠广袤的土地本就是中国的、连你小子也该是中华民族耗子的子孙!待弯腰拾起一土块准备击打那鼠时,再看,现蒙古国土地上、这个曾经中华民族土地上叛类的子孙早己知趣地钻地遁形无影无踪了。
“撤吧”!“别!都到这了怎么也得出趟国吧”。
心领神会。四泡雄性如注之水呈弧线昂扬越过国境浇在了曾经中华的大地上。
四、一线水,二线水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但这,却是久远了的歌中的故事和久违了的诗中记忆。
当年,我所寻觅的边防雷达部队之路远比今天要长了许多、条件也恶劣许多。我所见到的边防33团和28团雷达兵们的真实生活状况以及雷达连所处的生存环境绝非想象之中的诗意和浪漫。
“草原四季两场风,从春开始刮到冬”。那个年代草原上的天气冷呀,能冷到你感觉是从外到里逐层都在“发热”,热得只有心脏是冰凉的。不象现在,又什么地球热效应、又季风回旋、海平面上升啦,恨不得现在全球都在出汗。那时到内蒙边防的印象是,撒尿你都得挑个好时辰、找个好角度,否则将遗害无穷。
内蒙,大抵是从头年的九月下旬就银装素裹漫天皆白进入了冬季,到次年的五月份仍是大棉裤大棉祆一样都不能少。这期间边防连队的饮水保障、给养运输、油料供应如遇到“没膝雪”和“白毛风”就成了真正的大问题,化雪水、砸水泡子取冰化水更是在此当兵们的必须经历和必修功夫。上面白毛风,地上冰和雪,为了水,战士们要坐敝棚大卡到几十里以外的泡子中去刨冰。来时,战士们穿戴严实、干干爽爽,包包裹裹,扎在一堆儿一付“熊”样,可刨冰过后却个个汗流满面,里外皆湿。刨完的冰装上车,人得坐在冰上返回,再加几十里地的白毛风一吹,上下夹攻着那是一幅啥光景啥滋味可想而不可知。
水,对这里的雷达兵是太重要了,不仅要保证人的生存,更要优先保证维系天线的转动,保证雷达开机柴油发电机水箱的用水之需。 己然如此恶劣条件,机器对水的“卫生标准”也就没有那么尅克了,但这刨回的冰、化完的水是还要入口保证人的生存的呀!眼瞅着冰晶晶的驴球马蛋、羊粪和牛屎渣子镶在其中而无别的选择。本来嘛,这水泡子里的水在未成冰前就是人家草原上牛羊猪马的所有,夏日里牲口们暖洋洋地在水泡子中边喝边拉边尿边洗澡,你这刨回来的本就是人家牛羊猪马冰冻后的洗澡水而己。
有油,就能开机。有水,就能安全运转。某种程度上讲,一线连队“还好”,因为一线,有了特殊的职能,也就有了相对“特殊”的保障。首先,你一线雷达要保证24时开机常备值班,所以,这柴油发电机就必须一天到晚都得“突、突”着。“突突”出了电,当兵的屋里也自然就“突突”出了光亮,虽然那昏暗的灯泡只有25度。但只要柴油电机在运转、只要有水的保证,这一线的兵就还可以在规定的有限时间里洗个从柴油机水箱内交换出的“热能热水澡”。但二线的连队就没有了这份因地理位置带来的高等级“准备打仗”的得天独厚了。二线连队属“待命”开机的“非重点保障”单位,一般情况下“特区政策”倾斜不到二线,有点儿“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甘霖待降”的尴尬和寂寞。不让开机,就不能发电。到了晚上,除了天上的星星还亮着,黑灯瞎火的连地下的虫儿您都看不见了,还不就得早早的安歇着,更别谈有什么热乎水儿可以洗澡的奢望了。当兵的们在“孤岛”上翘首以望,就盼着从“浩特”那头的电线里传来“开机”这两个字。
五、黄花菜、鸡腿蘑
忍耐冰雪覆盖了一冬的草原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季节。草原上的草绿了,草原上的花开了,草原自己也懒洋洋、毫无羞涩地敝着自己的前胸,阳光下任由肆弄,对草原而言,这是一年之中怀春的季节。
东黄花山、西黄花山,这是汉人对草原深处两座圆鼓鼓、乳状的山包通常的叫法,而“黄花山”则皆因此山包之上那一丛丛、一坨坨,层层叠叠,漫山遍野,如炽如火,逢时便如约盛开着的黄花而得名。每到这黄花绽放的季节,空气都能随着蜜蜂那不倦的“嗡嗡”的声音在一起颤动。这时,战士们也如蜂般穿梭于黄色、绿色的海中,收获着这上天所赐的“纯天然”。采回的黄花经战士们用开水淖过去毒、日头曝晒后便成了上等的准黄花菜,再装进印有“航空旅行”字样、上海产的合成革拉链旅行包内,单等雪封之前各自探家时送给亲朋好友。
由锡林浩特告别草原南下,一路行驶在坝上。中途“放水”减负,见脚边一丛圆圆、白白的东西,问:“什么东西”?小司机挺了挺胸大肌略现单薄的胸脯:“口蘑,鸡腿蘑”。“能吃嘛”?“鲜着哩”!“那还等什么!采呀”。“这的不干净,路边土多,洗起来麻烦,吃起来牙碜”。话语不多的小司机此时俨然老资格的“小老蒙”:“我带你采去”。我刚点了颗“牡丹”叨在嘴上,那边小司机就己在离开道边三、四十米远的草丛中向我招手了。
嗬!好大的一丛蘑菇,白嫩嫩、肉乎乎,比肩扎堆,阳光照射之下泛着迷人的光。我小心地拔起一个拿在手里惦了惦足有二两多重,个头如大灶中的白馒头,茎柄粗圆,肉厚且甆实,散出异样的香味,绝对一标准大号“鸡腿”。 小司机脱下军装捡中等个的包起了七、八个,起身向路的另一侧跑去。路的对面,大概同样的位置上也有着一丛长像几乎相似、个头大小同等的蘑菇群。十来分钟时间我和小司机己兜了满满地一军装蘑菇回到车上,小司机打开后备箱腾出了一个装满军用罐头的纸箱子,将这一大兜蘑菇细心整齐的码放了进去,一数整整40个。“上车吧,咱们得往回赶了。不然....”车上,小司机告诉我:大的蘑菇是不能采的,因这种蘑菇味道极其鲜美,那些大个的蘑菇你只要采下来就会发现己开始“生虫”。那些个头小的,一是还未长成,味道欠佳。再说了,咱不是还得给后来人留点念想吗。在这儿采蘑菇有个决窍,只要你在这边采到了一丛,那在与其对应的位置上一定还会有另一个相同的一丛在等着你。原来这蘑菇生命得己延续的苞子粉是呈对称崩开播洒的。我们之所以赶着时间下坝其实也只是怕刚采下的蘑茹自己开始“长肉儿”。
当晚,在张家口就着一瓶白酒品尝了这刚采下的鸡腿鲜蘑的美味。一盘“鸡腿鲜蘑烧肉”、一盆“鲜蘑菇老汤”,风卷残云般入腹,口上鲜香无比。
吃过东西南北的蘑,品过山上树上的菇,但至今日还没能再尝过可以超越这次自采鲜鸡腿蘑的美味口感。味之美、口之鲜而百思不得其解。数年后终有所悟,其鲜、其香大概皆因所采鲜蘑中不断快速生长而出的小虫们所为。其实,当晚至张家口驻地时,40个碗口大小的鲜蘑之中因“新生命”们探头探脑的大量诞生而不得己将其淘汰过半,留下做菜、煲汤、入口剩下的这一半中则是两眼一闭,容“新生命”们一起入锅、入味,原“虫儿”化原食的自欺欺人罢了。此味奇鲜、奇香定是由那些与鲜蘑一同殉情的“虫儿”们的存在才变得美味无比的吧。
六、“神枪手”
那个年代去内蒙、下边防其实还有两件乐事儿。一是可以骑马,二是可以打枪。
下边防的一般都是从“上级机关”而来,常言道:宰相家人七品官,人家“基层部队”的人对“上边下来的”都跟根儿葱似的“供着”。但咱自己得知道自己有几块豆腐高,千万别不知天高地厚真拿自己当颗葱先自己给自己“拌上”了。既使这样,人家“基层部队”的同志还是会纯朴到将你高看了。比如,引你到了牧民的蒙古包里时也不忘在称谓介绍之前加上一句:这是北京来的“答拉嗄”。
“答拉嗄”,蒙语意既“干部”。你想想,过去蒙族老乡们在包里见到的都是被“驻军连队首长”们介绍认识的、从“浩特”里来的驻军首长们的首长,今天,这首长们的首长亲陪并介绍从远方来的这些“答拉嗄”们岂不稀客。纯朴好客的蒙族老乡们大多会厚道的有点受宠若惊的端上自酿的马奶子酒和用奶子腌制的沙葱、沙蒜,奶皮子,奶豆腐,条件好的还会当场牵出一头“替罪的羔羊”给你整出一大盘手抓肉来,但这个时候你千万万可别忘乎所以,因为在后面的是一碗一碗伴着祝酒歌、举过头顶敬上来的“草原白”。
去草原,马是一定要骑的。但你骑的马,未必是草原上真正的马--烈马。给你牵出来的一定是那些年华己逝、风韵全无的大肚子马,或是己经开始进入颐养天年年龄段的老马。这所骑的马又可分出两类,“走马”和“跑马”,先别晕,草原上确实是这么叫的。骑在“走马”之上,就如同骑在平衡木上,只觉那碎马步亦步亦趋紧倒紧走,但马的身形不乱,平稳扎实,不颠不跳,有点像架弄着的马术表演,又如同坐轿一般。要是赶上“跑马”那您这次非晕不可,虽不至弄个自残,但不消一刻功夫那两瓣的腚就得给你颠成四瓣,下得马来非“拉胯”不可。
草原一望无边,地广人稀,不象在内地里整出点枪声来就是政治上的大问题 。可以说,凡下过草原的“达拉嗄”们,几乎没有几位没在那儿过过枪瘾的,但能打出名声、打出了“称号”的却不多见。我当属于一例外的“三枪传奇”。草原上一圈下来,因打下过天上高飞着的鹰的翅膀根,月夜之下打过水泡子中惊起的野鸭的脖子和打过突然跳起来逃命的兔子的脑袋而得名草原“神枪手”的口头赞誉。
单说这兔子和鹰的事。
到了草原,被地主们盛情款待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打猎。背上一军挎子弹,再扛上两支半自动,车一开出去就是二三十里远。说是打猎,但由于生态的恶化和长期的滥打滥捕,偌大的草甸子之上哪还有什么猎物可言。鸟被打飞了,兔子打精了,就连原来成群的黄羊也被“有组织的”猎杀打到国境线的那边去了。没了猎物的“猎人”就像猎物本身一样幽灵似地在草甸子上游荡,有时真恨不得给自己也来上一枪以感受一下鲜血涌出的畅快和期待。
偌大的甸子之上静的只有空气的声音,因捕食不到猎物而尽乎绝望的鹰也只能无奈的落在国防通信线路的电线杆上受着日头的煎烤,阴鹜的眼晴死盯着这几个闯进了本该是它自己领地的不速之客。电线杆上那原本草原的主人和持枪的偷猎者们就这样死死地、一上一下的对视并互相揣摸着。最终“这地上的”还是先忍受不住那“杆上的”高高在上和那孤傲的目光,“哗啦”一下将子弹推上了膛。“嘭”的一声,不知为什么,空旷的草原上半自动发出的声响竞没有子弹出膛的清脆和撕裂空气的尖啸声。子弹是以45°角射向空中的 ,毫无目的的虚张声势。别说电线杆上落了只鹰,就是那上面坐着一只兔子你也不能去打、不敢去打,万一碰上个“二五眼”再让不长眼的子弹打断了国防电线那可就是天大的罪过了。让人想不到是,枪声过后竟飞起了一大一小两只鹰。原来在地上的草丛中还有一只七八十公分高、个头略小点的鹰。这一枪将那只曾与之对视过的鹰给激怒了,只见它占尽空中优势,在这几个闯入者头顶的上空翻飞着、愤怒的尖叫着。
“反了你了”!“嘭,嘭”两声枪响过后,天上飘落下几片灰褐色的羽毛,“空中优势”凄漓地叫着拉杆升到了高空。那个小个的、从草丛里飞出的鹰显然是想与那个“空中优势”呈编队飞行,但终因不属一代型号而只能在中空区域里盘旋。“啪、啪”这次子弹出膛倒是有了固有的清脆和明显传递给肩上的后座力,但这两枪却是朝着那个中空高度的小个子的鹰而去的。只见那个正奋力盘旋上升的“小个子”在空中紧紧地收缩了一下,跟着翻了个筋斗直直地掉了下来,只是在与地面接触的瞬间又突然展开了膀子踉跄着栽到了草丛中。跑过去一看,“小个子”瞪着如火的眼晴,近一米长的右半边翅膀伸展着、乎煸着,左半边的翅膀则无力地拉拢下来,翅膀的根部明显有一团殷红的血迹渗出并和杂碎的小羽毛粘附在一起,鹰,显然是被击伤后掉下来的。
胜利者们兴奋地、七手八脚着想把“小个子”抓住。“嗷”的一声尖叫,一位胜利者像是被电击了一样跳出了包围圈,再看,厚厚地冬军装罩衣上己经被“小个子”的利爪抓出了一条长长的口子,手背上也已渗岀了血迹。1 :1平,从天上打到地下的这第一个回合竞成了平手,谁也没比谁更多占到便宜。突然间,第六感觉得头顶之上有一个巨大黑影砸了下来,几乎是眼到枪到,“啪啪”两枪上去,己经快落到头顶上的“空中优势”给打了回去。“偷袭”!“快上车”! 这边“小个子”已被经验丰富的司机用军用雨衣捂住后塞进了后背箱里,胜利者们将“战俘”绑架着绝尘而去。又是“嘭”的一声,不过这一声不是出自枪膛,而是发自212吉普车的棚顶之上。一脚刹车停住后,212四门大开,“空中优势”几乎是同时腾空飞起又拉回到了高空,所幸那绿色的军用帆布棚顶没被开了天窗。
十几里路的回程几乎是与“空中优势”周旋着、相持着走走停停,但却再没有从半自动中出膛一颗子弹。
车内。“你说它俩是什么关糸”?“母子。要不就是母女”。片刻无语,却又几乎同时异口同声“回去给它包一下放了吧--”。
阵地上的雷达天线已悄然显现在眼前。“停车”!前排副驾驶座位上的我大声喊道。长长地“吱”的一声212站住了。距车头仅不到两米的地方一只黄褐色的野兔儿被吓呆了立在路的中央。那边驾驶座上的司机还没反应过来因为什么突然停下,这边的我己将半自动伸出了窗外,又是“嘭”的一声,只见兔子的脚边冒出了一股白烟儿,弹无虚发,子弹钻进了草原的大地里,兔子却钻到212的底下。咳!这个气呀。臭枪!下得车来往底下看,惊恐的兔子正伏在212的肚子底下喘着粗气。又是对视,不过近得连兔子眼中恐惧的血丝都看得一清二楚。“嘭”!又是一枪。终于,被打醒了的兔子用强壮的后腿弹出一个漂亮的跃起从212的前扛处飞了出来。臭手!近在咫尺却连放了两个空枪,岂不让天下的兔子们耻笑!
又一个漂亮的跃起,兔子在用尽平生的力量跃起以逃出这死亡的嘭嘭之声。“啪---”己跃至最高点上的这只成年的黄褐色的兔子以极其优美的跳跃、和在夕阳照射下泛着的一身金色的余辉、定格在这有着撕裂和尖啸子弹出膛的声音之中。子弹是从兔子的耳后洞穿进去、由三瓣嘴的位置贯通而出,兔子在离开这片草原的最后时刻几乎没有时间去感受痛苦,除了那两声嘭嘭中的惊吓。当兔子从最高点向下落时是那样的柔软,舒展,那样的轻,如草原上的空气。
..........
多年后的今天,面对生命、逝去和存留仍心在“忏悔”的反思着---谨尊世间生灵,从此不再杀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直到现在凡飞禽绝不入口,乃至生鸡、家兔柴锅美味概不入食,旨为年轻时的血性和过失买单。
对了,那个曾经被绑架过的“小个子”所幸没被伤及羽骨,后来被一时的胜利者们按住、并在连队卫生员的操持下对伤口消了毒,上了药,被包扎好。回过神来“小个子”又乘无人注视之际饱餐了几大块鲜嫩的猪皮肉之后体力似乎得到了恢复,在远远地、放生者们的窥视下成功“逃离”阵地,很快就融于月色初降的草原。
谨以此记,献给我们曾经的当兵岁月! 献给我们的边防雷达兵! 献给广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