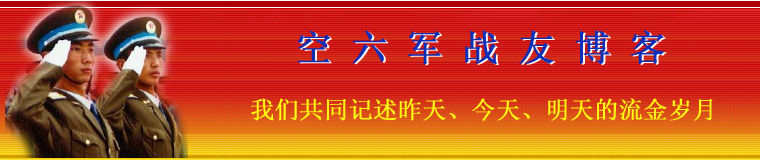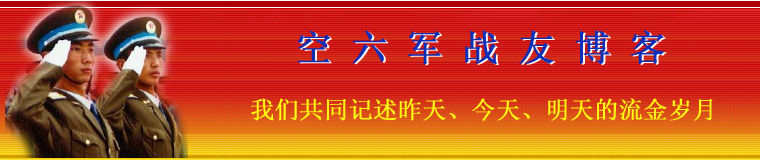阿敏这人很拧,离开天津之后,一直给我写信。但每次收到她的来信我都坚持不拆不看,立刻退回,(当时在邮局工作退信也特别方便)更没有给她写过任何回信,这么做并非我心狠,主要是我不想让她对我,对我们曾经的感情继续存有哪怕一丝的希望。我希望通过让她看到我的绝情,彻底斩断了她对我的情丝,以便可以让她尽快放下我这个感情的包袱,重新开始爱的选择,重新开始她的生活。
阿敏是个十分倔强的女人,尽管我每次都退信给她,但她给我的信还是不断邮寄过来,当时我的同事们都知道退信的事儿,只要看到宁夏石嘴山邮局写给我的信,他们就会立刻扣上一个查无此人的印章,然后退回给寄信人。
就这样,信还是隔三差五地不断地来,我还是继续保持着沉默。大约在连续收到她来信半年之后,信件突然断了。断的是那么干脆,那么彻底。我不知道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我担心过也惶恐过,甚至也通过她的好朋友王娜问过她的情况。但王娜当时也说有好久没有和阿敏通信了。有一次太过担心阿敏会有什么意外,我悄悄地拜托佟楼邮局的吴瑛尝试着给石嘴山邮电局挂过一个长途电话。那边回答说阿敏早在大半年之前就调回银川了,具体去了那个局,或者是否仍然还在邮电系统,那边都说不知道。
又过了几个月,我意外又收到了她来的一封信。由于特别想立即知道她的近况,这次我破例拆开了信。她在信里告诉我说,前几个月她由于感情的挫折,身体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身体彻底垮掉了。后来大病了一场,并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给我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出院,并托父母的关系调回了银川邮电局的包裹科。
她在来信中还告诉了我,她已经彻底放下了跟我的感情,今后再也不会跟自己较劲了,这次生病住院就是因为太放不下这份感情,以至于最后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都错乱了,医生也告诫她此次出院之后,不能再想过去的事儿了,要彻底的振作起来。只有这样,身体才能彻底恢复如初。
考虑到她的年龄和身体的情况,阿敏的妈妈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位年龄偏大的工厂工人,人长相很粗,也没有多少文化,就是银川一个焦炭厂的炼焦工,两人已经见面走动了一阵子,现在正准备筹备婚礼。估计很快就会成家了。看到信的这里,我终于松了口气,前一段突然为阿敏紧绷的精神也彻底得到了放松。
虽然说是得到了心灵的释放和解脱,但迄今为止,我都总有一种莫名的负罪感。虽然在东北学习的时候,我们也只是偶尔拉过手,从没有过丝毫的“越轨”行为,虽然阿敏的感情基本都是她单方面的想法,虽然我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当面对阿敏做过任何感情的承诺,但我还是经常感觉自责。特别是好多年以后,当我从阿敏的好友王娜那里打听到了一些有关阿敏之后生活上的一些坎坷、遭遇和变故后,心里的那份本来就挥之不去的自责就愈发变得沉重起来。
据王娜后来介绍说,她和阿敏一直保持着通信,所以对她的生活现状一直比较清楚,阿敏自从离开东北邮电学校之后,也一直将王娜作为自己的知己,两个人无话不谈。王娜说阿敏在追求真爱无望之后,在年龄不允许再拖延婚姻时,仓促地和一个石嘴山同城的一个工人结了婚,同年生下了一个女孩。本来这应该算是了却我一直纠结和歉疚的心,然而阿敏后来的日子并像常人那样过着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王娜说阿敏的孩子还没满三岁时,她家就发生了意外。丈夫经常酗酒,每次喝多了回家总要拿阿敏出气,非打则骂。为了孩子阿敏一直忍受着那永无休止的家庭暴力。后来那位在焦炭厂上班的丈夫终于有一次喝醉了酒之后和别人打架,结果把对方打成了残废,就这样她丈夫因为醉酒伤人被判了十年的重刑。
原本两人感情就没有什么基础,加上长久以来的家庭暴力,现在又被判刑要入狱十年,如此一来,阿敏彻底绝望了,最终选择了结束这场悲剧式的婚姻,之后自己一直辛苦地过着单身的生活,直到后来把女儿拉扯大,最终考上了大学。孩子上大学的那几年,她一直坚持着业余时间多做一份工作,多挣些钱维持家用。日子一直过得很辛苦。
1991年王娜给我电话说阿敏的弟弟来天津办业务想跟我见见面。我在天津的利顺德饭店请她弟弟一起吃了饭。她弟弟名叫赵健,也是个大高个子,弟弟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银川的一家房地产公司打工,很受老板的重视,但之后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倒闭,小赵就没了工作。这次来天津是他姐让他来找我,看看是否有什么工作的机会,帮忙给小赵介绍一下。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在海南做房地产的朋友,算是给阿敏的弟弟帮上了忙。
之后又过了几年,我去了加拿大,有次回国换手机,恰好看到阿敏弟弟赵健的电话号码,就打了个电话过去问问他姐的情况,那时候赵健已经回到了银川。他说她姐姐一直供女儿上完大学,又帮女儿成了家之后,自己提前从银川邮政局退了休。过了一年之后,她感觉累了,于是选择了再嫁。找了一个比自己大20多岁的退休老人远嫁到了青海。
听到阿敏这些人生坎坷,心里隐隐地感到了伤痛,客观地讲,她的一生如此不快乐,命运如此多舛,虽然不是我亲手毁了她的情感和生活,但我确实是她的生活中的一个不幸的源头。她的命运的确是从她认识我以后才发生了一系列的不幸。以后的日子里,这种自责始终折磨着我,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心里总像压着一块大石头。